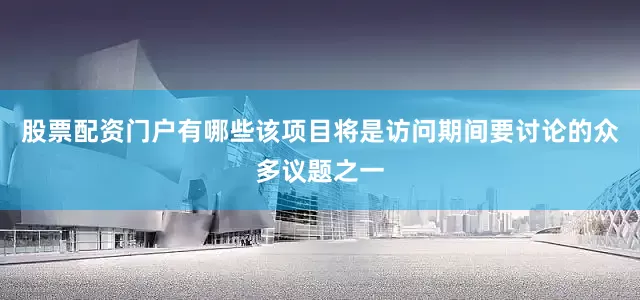天津日报记者 徐雪霏
在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东西陈庄村,一门源自明代的古老技艺——仿古青铜器失蜡法铸造技艺,正以顽强的生命力跨越时空,在当代焕发新的光彩。这门集历史、艺术、技艺于一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不仅见证了村庄的兴衰变迁,更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。
百年匠心
古法铸造仿古青铜器
东西陈庄村的铸造历史可追溯至明代建村之初。彼时,村内小作坊便开始铸造农具、生活用具及古典人物造像等,奠定了金属铸造的工艺基础。真正的技艺飞跃发生在20世纪中叶。1968年,村办铸造厂成立,厂中元老蔡勋师傅成为技艺融合与创新的关键人物。1978年后,村办铸造厂中独立出金属工艺品厂,开始专门制作仿古青铜工艺品。随着旅游业兴起,仿古青铜器需求激增,以张生、郑建民为代表的第二代传承人纷纷开办工艺品厂,将这门技艺推向产业化发展的高峰。
“听父亲说,高峰时期,村里有18家工艺品厂,带动就业1300多人,年产值达6500余万元。”东西陈庄村仿古青铜器失蜡法铸造技艺第三代传承人郑长利回忆道。这门技艺不仅富了一方百姓,更让东西陈庄村成为京津地区闻名的“青铜工艺之乡”。
失蜡法,又称熔模铸造,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制作的核心技艺之一,其精髓在于“以蜡为模,以铜铸形”。东西陈庄村的技艺传承者们,在坚守古法的基础上,不断优化工艺流程,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操作体系。整个制作过程包含十余道精细工序,环环相扣,缺一不可。每一步都蕴含着匠人们数十年积累的经验与智慧,也正是这些看似繁琐的步骤,构成了这门技艺难以被机器替代的核心价值。
首先是模型制作。工匠需先手工塑造制品的模具雏形,如今也多辅以3D打印技术提高精度。接着进入最为考验功力的披模环节——工匠要对模具形体和图案进行精雕细琢。这一步骤直接决定成品的艺术价值。然后是制蜡模环节。精修是考验工匠耐心和眼力的环节。在强光照射下,工匠手持特制刀具,细致修掉蜡模表面的微小瑕疵。“有时候,一个复杂纹饰的精修就要花费整整一天时间。”郑长利指着一尊佛像蜡模的衣纹说,“这些流畅的线条,都是靠一刀一刀慢慢修出来的。”
接下来的披砂工序尤为关键。将精修后的蜡模固定在专用冒口上,放入特制泥浆中浸渍,取出后均匀撒上高温耐火砂。“披砂的厚度和均匀度直接影响铸造质量,”郑长利演示着披砂动作,“太薄了承受不住铜水冲击,太厚了又会影响气体排出。”这个过程需要重复六到八次,每一层砂的粒度都有讲究——内层用细砂保证表面光洁,外层用粗砂增强强度。
披砂完成后,需要自然风干三到五天,待其完全干燥后才能进行脱蜡。脱蜡过程同样充满挑战:将模具放入烘烤炉中,缓慢升温至150-200℃,让蜡质完全融化流出。最后是浇铸环节。将铜料在900℃的高温下熔化成铜水,这需要丰富的经验判断铜水的成色和温度。铜水要像镜子一样亮,泛起细细的波纹,这时候浇铸效果最好。师傅用长柄坩埚从熔炉中取出通红的铜水,稳稳地倒入模具冒口。整个过程工匠必须一气呵成,任何迟疑都会影响铸件质量。
浇铸完成后,铜制品需要冷却数小时才能脱模。工匠用特制工具小心击打外壳,露出里面的铜制品。但这还远未结束,接下来的打磨抛光更需要匠心独运。经过最后的上色处理,利用特殊的化学药剂在铜表面形成致密的氧化膜,一件精美的青铜工艺品才最终完成。
“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在师傅引领下,经过反复实践才能逐步掌握。”郑长利表示,“成为真正的工艺大师,不仅要精通铸造、模具制作技能,还需具备文化底蕴和美学、绘画、雕刻、文物等多方面知识。”
铸古铭今
非遗技艺的现代化转型
东西陈庄村的工匠们用他们的巧手和智慧,创作出了一大批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工艺品,这些作品遍布全国各地。
其中,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和平广场的抗战纪念墙堪称巨作。这座由郑长利主持制作的纪念墙,由六面墙体组成,包括五面抗日战争大型浮雕墙和一面抗战将士手印墙。墙体总长220米,青铜浮雕总面积达500平方米,用铜近50吨。浮雕生动再现了从1931年“九一八”至1945年抗战胜利的艰苦历程,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。“为了塑造抗日战士的表情,我们反复修改蜡模数十次,”郑长利回忆道,“眼睛的神采、肌肉的线条,都要做到传神。”手印墙则镶嵌着抗战老兵的手印及签名,成为历史的永恒见证。
另一件代表作是2018年为北京市第八中学制作的高3米的孔子像。雕像神态庄重,衣纹流畅,完美展现了至圣先师的风范。“孔子像的衣纹是最难处理的,”郑长利说,“既要体现布料的垂感,又要展现人物的气度。我们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,最后决定采用汉代画像石的表现手法。”
近年来,传承人们还在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。郑长利创作的《铸古铭今·清风武清》便是一例。作品以铜铸摆件为载体,中心饰以象征清廉的竹子图像,两侧以活字印刷方式刻有“秉文兼武,清廉奉公”字样。“竹节的铸造特别考验技艺,”郑长利指着作品解释,“要表现出竹子的挺拔与节节高升的意境,每个竹节的角度和长度都经过精心设计。”
其他如北京雍和宫铜鼎、颐和园铜亭、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奥运铜雕、中华世纪坛直径2米铜钱等作品,都以其精湛工艺和文化内涵,成为东西陈庄村青铜铸造技艺的名片。
然而,这门古老技艺的传承发展正面临着严峻挑战。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和市场需求变化,东西陈庄村的青铜工艺品工坊已从高峰期的18家减少至目前的8家。虽然郑长利、郑长保、荣军等八位工坊负责人仍在坚守,但整体规模已大不如前。
“要培养一个成熟的工匠,至少需要五年时间;而要成为真正的工艺大师,更需要数十年的磨练。”郑长利一边指导徒弟打磨铜像一边说,“现在年轻人多向往大城市生活,愿意沉下心来学习这门复杂技艺的越来越少。每一个蜡模雕刻的学徒,第一个月可能都在学习如何握刀。”
与此同时,市场竞争日益激烈,机器大规模生产对传统手工制作形成冲击。工坊的产品虽品质优良,但成本较高,在价格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。“机器压制的产品一天能做几十件,我们手工制作一件就要半个月,”郑长利算了一笔账,“但手工作品的神韵和艺术价值,是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。”目前,产品主要销往东三省、山西、内蒙古及河北地区,市场拓展面临困难。
面对这些挑战,当地政府和传承人正在积极寻求突破。东西陈庄村党总支牵头成立行业协会,指导工坊向工作室方向转型,对符合条件的工作室进行授牌,将其发展为旅游参观点。协会还组织工匠申请非遗项目,进行品牌打造,推动技艺价值提升。
在传承方面,东西陈庄村的工匠们在坚持“师傅带徒弟”的传统模式的同时,也开始探索与学校、社区合作开设工作坊和培训班,吸引年轻人了解和学习这门技艺。2023年,传承人制作的铜造像代表武清区参加“海河工匠杯”第四届“通武廊”技能大赛并获得优秀奖,为技艺推广提供了新契机。
展望未来,郑长利认为,东西陈庄村仿古青铜器失蜡法铸造技艺的保护与传承,需要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结合。一方面,要坚守技艺核心,保持其文化基因不变。通过建立数字化档案库,对技艺流程、技巧和相关知识进行完整记录。“我们正在用3D扫描技术记录代表性作品的每一个细节,”郑长利展示着电脑中的三维模型,“这样即使实物损坏,也能依样重铸。”另一方面,要推动技艺创新,使其与当代审美和市场需求相结合。鼓励工匠在传统基础上开发新产品、新设计,拓展应用领域,如文创产品、城市雕塑、家居装饰等,增强技艺的生命力。“我们不仅要传承技艺,更要让技艺活在当下、服务当代。”郑长利道出了所有坚守者的心声。
千年技艺,薪火相传。东西陈庄村的仿古青铜器失蜡法铸造技艺,承载的不仅是一门手艺,更是一种文化记忆和精神血脉。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,这些当代工匠们正用他们的坚守与智慧,让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,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书写着生动注脚。正如那经过烈火熔炼、精工细琢而成的青铜器,这门技艺本身也在时代熔炉中经历着锤炼与升华,必将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更加璀璨的光芒。
欣旺配资-股票杠杆网-郑州股票配资网-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